虽说一直都知道世事难料这句话,但是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让我再一次深切体会到了这句话的重量。
这些年来,虽然我并未停下寻找的脚步,但是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和自己对人性的要求,让寻找的路变得非常艰难。世俗的评价也好,自己对本质的了解也好,都在不断告诫我【不要走进婚姻】。虽然我自己热爱家庭生活——或者说喜欢文艺作品中所描述的sweet home的图景,但是我悲观地感知到这些图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的实现多靠一方无底线地容忍与让步。而在现实中,做出这些牺牲的往往是女性,她得到的奖励不过是几句赞美,或是年老力衰后所谓的天伦之类,女性对家庭的付出往往不能被正视、尊重,当她走入婚姻这个领域,女性的【自我】就消失了,她变成了【太太】、【妈妈】、【儿媳妇】,她被其他所有人定义,离开这些人她无法自我定义——就像发生在我家里的事情。
我承认,有许多女性喜欢这样的生活,或者认为能够支持家人也是莫大的幸福,但是,从未走过的路,如何断定那就是不幸呢,她没有尝试着自己定义自己,又如何知道自己并不值得被支持着做一些事情呢。
到了这个年龄,他人的言语、意图都变得非常透明,对方说的每句话我都能清楚看到他想要我回应什么,这些回应里并不包含对我的尊重和爱,有的只是对付出的疲倦与厌恶——顺从社会的男性会受到表彰,这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个社会恰恰不要求男性对女性的付出与尊重。
在我的上一段,也可以说唯一一段感情中,我阐述过一个道理,不可以用前人的错误来惩罚后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之前遭遇的苦难与背叛和现在到来的人无关,不该用陈旧的评价系统来应对新人。但是绝大部分人做不到,他们在别的地方收获了不堪与疲倦,却要将原因全部怪罪在我这个无辜的人头上——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呢,仅仅因为我是女性?
在父母祖父母日复一日的期待中,我们的时间毫不留情地溜走了,尤其是疫情这几年,仿佛大风刮过什么都没留下。一直坚持的工作因为突然间的放开,所有人全部感染,被悄无声息地锁进了柜子,不再去回顾、表彰、怀念,不算错,但所有人都不再提起我们的付出。生活中,我从30岁的前半走到了30岁的后半,许多事情都与我无关了,我的人生仿佛进入了一种什么都抓不住,但又什么都不必在乎的状态,我不太想去考虑太多的事情,但是淡淡的悲伤与惶恐总是如影随形,因为许多事情都进入了倒计时,比如祖父母的寿命、父母的年龄、我的育龄。
谈论这些事情是非常艰难痛苦的,当我意识到60多岁的人很快就要到70岁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慌。我的外婆因病不到80岁去世,我的外公患病多年,几位子女一起照顾,也在前年去世了,虽然他活到了87岁,但是对比父母的年龄,似乎也并不是遥遥无期的感觉。尤其是爷爷奶奶,奶奶的身体大不如从前,这两年更是显得摇摇欲坠,爷爷身体硬朗,但毕竟已经老了,没有人能为他们的人生做保证了。
在我的认知里,仿佛父母一直都是四五十岁的样子,不会老,总是乌黑的头发,矫健的身躯。但是当我有一次看到母亲为父亲染发,父亲的头发也白了许多的时候,我才深刻体会到,父亲老了,尽管他身体健康声音洪亮,对世界保持着好奇,甚至身体看起来比我还强壮,但我知道他老了——我们出门去,再也不用他等我了,他也抱不动我了,我站在那里,看着比他还要壮——我再也不能当一个小姑娘了,我开车,我采购,我做各种事,我仿佛也在慢慢撑起这个家。
我的父母都是很爱我的,我也是在他们饱含期待中降生的,只是年代、文化、性格、环境、经济的关系,我们以前总是过着兵荒马乱的感情生活。他们先没有处理好自身的相处问题,又迎来了我和弟弟两个家庭成员,于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搅在一起,家里似乎每天都在吵架——我一直说自己非常粗糙,但我内心深处明白,如果我不将自己变得粗糙一点,我可能都无法度过非常痛苦的那段时光,尽管现在看起来那只是生命中非常短暂的几年,但是当时却觉得这种日子仿佛要天长地久地过下去——对小孩子来说,即便是两三年也是非常漫长的。
亲子关系也好,亲密关系也好,都是我甚至直到现在也难以处理好的课题,所以我恐惧去发展新的完全敞开的亲密关系,我心灵的所有门窗都关闭了,在昏暗中我才觉得安全。我无法想象,我自己步入婚姻,重复着一边对付伴侣、一边应付孩子的生活,同时还要兼顾前几十年完全不认识的所谓的【对方的亲戚】,每一件事都让我觉得无比的疲惫——相信一个人、容忍一个人、宽恕一个人,光是想象都觉得精疲力尽——活人不是纸片人,纸片人才是相信、容忍、宽恕的那个人。我花了30多年才与父母磨合到了今天的程度,一想到要再花30多年和一个陌生男人去磨合,痛苦就好像立刻扑面而来令人难以忍受——父母和我能够互相体谅、容忍,能够毫无怨言地为对方着想,那是我们在天然的血缘关系上又经历了30多年共同的酸甜苦辣时光,哪里又去找这样一个人呢,没有分享过的岁月无法支撑起长久的脚步。
这些年,我学着对自己更好些,学着接受自己,接受我的世界,我为自己划下非常严格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内我依然非常温柔温暖,但这界限之外的事情我不再关心。他人的悲痛喜乐,世界的风云变化,这些都与我无关了,我不再试图去让别人理解我,我也不再去理解别人,当世界变成可用与无用两种简单的选择之后,生活也变得舒适起来。我不追求太多宏大的理想或概念,我接受自己是一粒尘埃的事实,这粒尘埃在消融于历史长河之前,尽情地享受过就好,消散的那一天该去哪里她自然会去的。
或许是这些年家里经济条件好一些了,大家也都变得心平气和起来。虽然我并没有按照父亲的设想去谋得一个更有保障的职位,但是现在的工作也算是平稳闲适,尽管它有诸多的纪律束缚,以及编制的鸿沟,但是总体来说不太差,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焦点的转移,编制的问题也不再可望而不可即——其实无论是否真的有编制,父亲总是希望这份工作能给我更多的保障,尤其是在我或许无法拥有婚姻的现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能够代替家庭给个人许多的关怀。他终生被这个组织所保护,他也希望我能受到同样的保护,我明白。所以我在这里八年,经历了许多人的来来去去,有相处的非常开心的同事领导,也有非常不开心的时刻,尽管有时候嘴巴上也会抱怨工作,想要离开,但是我在心里依然对这里非常有归属感。
弟弟去了北京工作生活,最近家里也凑钱给他买了房子,希望他能依托着房子早点找到一个好的伴侣,在异乡过上平稳的生活。尽管他都30多岁了,但在我眼里,他还是个好小好小的孩子,尽管他在北京有着显赫的工作,赚很多钱,生活又规律,也很健康,但是我们总觉得需要有人陪伴他——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尽管我和弟弟在大学之后,其实并没有长时间在一起,甚至因为他之前的恋情的关系,他对我内心有一些怨言,但在分别了许久的现在,我们依然是最亲密的家人——我时常想着,我们努力培养他,培养的那么优秀,然后他就去了远方,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了,我还有父母可以互相陪伴,但他一个人怎么办呢,他必须有一个家,必须有属于自己的新的亲密的家人,即便这意味着他将要离开我们。
我以前总是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是来自于同一组基因,但是却要因为社会的划分成为外人,他要去成为别人最亲密的家人,从此我就成了他生命里的过客。我是爱他的,他也很爱我,但我们却都必须去往陌生人的怀抱。就像我看到许多女性在结婚后就彻底失去了栖身之地,她游荡于两个或三个家庭,直到其他所有的家庭都破碎了,她才能彻底拥有自己的家庭。
妈妈在外婆去世之后,对外公的照顾有增无减,外公在脑溢血很多年之后,又诊断出肺癌,在治疗之后又生存了八年,最后在农村老家穿上了他的最后一身衣服。我对外公的感情是有的,但是并没有很强烈。那是一个有些糊涂的老人,他认为我家的条件更好一些,而舅舅家总是不行,于是更多的关注都放在表弟表妹身上,但这母亲早逝的不幸的两姐弟,因为父亲的不负责任,爷爷奶奶的无限制纵容,变得无法管教,而在外公朴素的观念里,这两位才是他的血脉继承人,而我和弟弟则是外人,甚至于他的女儿我们的母亲也是外人,他可依靠的只有他的儿子们。母亲也曾为他的偏心糊涂生气,但是在最后的时间里,所有的恩怨都随着外公的生命流逝掉了,他睡在了为他准备了多年的棺木里。母亲和舅舅们一边哭着一边还要主持盛大的葬礼,在最后一天盖棺的时候,我们围着他进行了最后的道别,那副熟悉的有些糊涂的面容已经失去了红润的颜色,他变得像一根羽毛那样又苍白又轻,在所有人的泪水中回到了地母的怀中。我以为我不会流太多眼泪,但在进行仪式的那十天里,我依然可以轻易地哭出来。母亲展现出了一个女儿能做到的最大的悲痛,我们总是跪着守灵、念经、迎客,在下葬后她又几步一跪哭回了家里。她说她再也没有父母了——外公一直住在小舅家里,她每天必然要去那里陪伴老父亲,我上班的时候她已经为我做完早饭去了,我下班了她还没有回家,所有买来的东西他总是带给外公吃,甚至连一包泡面也要让老父亲尝一尝,为此我们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总是离不开娘家——但是在外公去世之后,母亲再也没去过小舅家里了,她说,老人不在了,家就没有了,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家,自己不用再操心了——她终于长久地留在了我的家里,而代价是失去了双亲,这个她是异姓的家里,成了她最终的家。
我陪伴着母亲经历了外婆和外公的去世,我能体会到她的悲痛,外公已经去世两年了,但只要吃到好吃的东西,她就会说,可惜你外公不在了,不能吃到了;看到有新的科技成果能延长寿命治愈疾病,她总是说,可惜你外公走了,不然他还可以多享受几年。悲伤从她的脸上褪去了,但却深深地潜入了她的心底,只偶尔从唇间冒出思念的星光。
我为这样的转移感到悲伤,似乎女性一生都在寻找栖身之地,她无法同时拥有父母的家和伴侣的家。而我的父亲,他早早就认同了我们的四口之家才是自己的家,他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把我们养活长大,又取得了职业的荣光,这个家是他所建立主宰的领地,而我们是他生命之树上结下的硕果。
去年,奶奶的情况不太好,爸爸说他早已做好了奶奶随时去世的准备,但60多岁的二叔却说他无法接受母亲会离开这个现实,于是留在老家照顾了很久奶奶。之后因为疫情放开,二叔在老家感染了阳性,二婶因此非常抱怨我们,因为二叔也已经有了孙子,他一年间许多时间要去北京照顾女儿女婿孙女,剩下的时间本应和二婶过自己的平稳日子,但他又要亲力亲为去照顾奶奶——二婶的父母也都已经去世了,她看顾着病弱的父母付出了近二十年时间,之后又要操心自己女儿的归宿,再之后是女儿的女儿,她的一生也总是奔波在几个家庭之中非常劳累,好不容易可以和二叔可以过几年太平日子了,二叔又要回去他的家里照顾父母,那她的家又在哪里呢——二婶和奶奶没有相处过,非常陌生,她的一生都徘徊在父母和丈夫的家里,如果丈夫离开这个家,那她的家又在哪里呢。
人的一生似乎就是这样东走西顾非常辛劳,但付出的人却不以为苦,他们只期待能用自己的辛苦换来更多相处的时间。从前我学习社区相关知识的时候,看到书上说,家是构成社会的最小单元,父母的家庭分裂成另外一个家庭,旧的家庭消散,新的家庭建立,社会就这样不断新陈代谢,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短短的几行字,不带任何感情,仿佛我们看着水面的泡泡形成又破碎,那么自然那么不值得在意,但是在这后面的割裂破碎却成为多少人心里的伤疤,成为他们的一生之痛。
我很惧怕去创造一个失败的冰冷的家庭,我曾经以自尊保护了自己的心灵,但在大多数的关系中,这层自尊又变成了阻挡他人靠近的冰层,我拒绝了伤害,同时也拒绝了爱——只要不受到伤害,爱也变得可有可无了。而我这些年看到的,大多数婚姻背后都藏着一个哭泣的女人,我的许多同事离婚了,她们带着伤痕和孩子,回到了父母的家庭,或许她们终于找到了栖身之处,但是伤痕又哪是那么容易消散的呢。
这些年我和母亲的关系完全转变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们是最大的敌人,我的绝大多数痛苦都来自于她,她也觉得我不是理想的女儿,不听话,不温柔,不乖。但是随着弟弟去往远方,以后也不会再回来,这家里只剩下了我们,她再怎么爱弟弟,也是鞭长莫及了,所以她的关注都给了我。而且在父母的观念中,弟弟在寻找伴侣上总是有优势,而我的选择范围却越来越小了,我的归宿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执念。
但我却无法改变。
弟弟曾经说过,如果你不满意现在的家庭,就自己找个人创造自己的家庭。那时候虽然我还没有很成熟,但是依然无法认同这个观点,我说,我不能为了跳出一个火坑而跳入另外一个火坑,从一个已知的火坑走入一个未知的火坑,再将我的痛苦延续下去,而且有极大的概率,我为了逃离第二个火坑还要再回到最初的火坑,那我怎么说呢,我自己选择的,我无法背负,又要被别人嘲笑吗。随着时间的流逝,父母老了,家里的经济慢慢好起来,我成熟了,许多矛盾也消失了,离别与美好的未来让我们的关系越发紧密起来,以前像天一样宽广的父母的双臂,也搭在了我的肩上,甚至于爸爸也会说,你真傻,你弟弟已经去北京了,不会回来了,家里的一切都是你的了,我们以后是要和你一起生活的,怎么会不爱你不考虑你呢。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他又变成了那个把我抱在怀里、扛在肩上的爸爸,而不是一直指责我不听话不努力的一天只相处几分钟的陌生的男人。
而母亲,随着她父母的离去,兄弟姐妹间的矛盾被放大,她的心彻底回归了我们的家。父亲退休后身体健康精力旺盛,脱离了组织的约束,天天都出去游乐非常开心,而母亲则不喜欢那些场合和应酬,她越发依赖于我的支持,当父亲蛮不讲理指责她的时候,说一些大男子主义的话的时候,我会立刻反驳他——因为我是他的女儿,他不会对我生气,但妈妈不是,同样的话妈妈说出来,他就会觉得损害了他的家主雄风。爸爸是很爱小孩子的,他喜欢我和弟弟,虽然他经常批评我、指责我,但是我知道,他心里非常爱我,同时为我的聪慧感到骄傲,所以尽管他年龄大了,脾气也大了,但是我能理解,我能包容,我知道如何与他相处。
奶奶年纪很大了,一个年轻时很刚强的人,也变得容易落泪。她总是为我没有好的归宿而担心,在她的认知里,一个女人,没有婚姻,就等于没有依靠,就等于悲惨,而父亲也总会这样想,他想要为我找一个能够像他一样爱护我的依靠,将我从他的掌心放入另外一个男人的心中。
但是这个未来似乎不会发生了。在经历了这么久的挑选与被挑选之后,他也承认,能够依靠终身的人太少了,大多数的依靠是贫穷时不得已的选择,而一旦条件好转,这依靠似乎也就不牢靠了。他之前一直处在社会的中上层,又在强力部门,上下等级森严,有时候会盲目相信他人的言语,直到退休后接触了真实的世界,才发现现在的男人和他那个时候不同了——当然,或许这也是因为,没有爱,所以付出就显得不足够。在他那个时代,责任是比爱更加庄重的承诺——或许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只是现在责任仿佛成了爱的伴生,不能单独存活。时代在变化,没有人能保持不变。
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依靠变得十分珍惜而稀少,世界从开放变得保守,曾经我们交笔友、交网友,许多人网恋,许多人一见钟情,但是现在这些都变成了【欺骗】的代名词——网络是无罪的,是人变了,所以载体也变得充满了危险与狡诈。社会逐渐回归了血脉传承的观念——生我的,我生的,才是可信赖的,其他人均为闯入的入侵者,要分享我已拥有的财富。不仅是男性这样想,经过计划生育的独生女性也这样想,夫权已经全面解体,父权在财权的入侵下也逐渐变质,以利益和血缘形成的纽带更加牢固。所以即便是父亲这样非常保守的第一代入城者也接受了【婚姻不是精准扶贫】的观念,甚至于对于结婚离婚的态度也非常开放,他总说,结婚找个依靠,找个伴儿就行,实在不行了,离婚带着孩子也能过,至少有个依靠——从依靠陌生的男人到依靠后代,他也不再盲目迷信同性。
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她总说,我有你照顾,可是谁来照顾你呢,你总要有你的依靠啊。尽管我觉得我可以安排好自己的一切,但是每次看到他们眼中的期盼和担忧,心中总是非常纠结,我既不想匆忙落入错误的关系让自己生活在无限的后悔与痛苦中,但也不想让他们总是为这件事操心,就像之前看小说里,季衡生了孩子要出去打仗,一方面他要完成自己的志向,但是一方面又为自己不能照顾孩子陪伴父母感到十分不孝而痛苦——无法满足自己喜欢的人期待无疑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知道这期待是纯粹的善意。
在拉扯了这么多年以后,这个问题以一种不能说圆满但是至少勉强可接受的方式将被解决。
上半年的时候,家里决定给弟弟在北京买房子,我买了快十年的那套房子也被挂出变现——那是我到现在这个单位工作之前买的,现在也升值了很多。那原本预定是我的婚房,没有装修,崭新崭新的房子,放着家里的一些杂物,我经常会过去看看,总想着有一天要住进去过自己的生活,但是渐渐地,我知道,不会有那一天了,无论卖不卖,我都不会住进去了——拖延太久的东西,就很可能不会再属于你了,就像我的汽车,当年说是为我买的,但八年之后,车子才真正到了我手中——但我没什么抱怨,毕竟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买的,而是父母的馈赠,尽管写着我的名字,但是它依然不属于我,我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拥有者,一旦有需要我就要让渡出去。
我经常会感到自己很贫乏,似乎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所以我不眷恋;但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拥有的太多了,我健康地活到了现在,我有稳定的工作,有父母兄弟,有可自由支配的一点小钱,我想要的东西总能得到,我不需要关心家里的财政状况,父母也都健健康康的,依然在为我们创造财富,我每天只需要吃喝玩乐上班就行了,没有需要我过分担忧的事情。所以大部分时候我并没有怨言。
但是无论如何,年龄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我不担忧父母,但父母总会担忧我,在为弟弟买到了称心的房子之后,他们也卸下了很大的负担,转过头专心考虑我的问题。
我以前总是嚷嚷着,要老公做什么,有孩子就行了,男人只是拖累,但当父母说提出说,去国外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还是被惊讶到了——我实在是想不到那么保守的父亲会率先想到这个方式,我以为这条路上最大的阻力就是他,但是结果却是他最先将这件事落地的。当他们说这件事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是开玩笑,但当他们从北京回来,寻找了好几条关系,最终选择在本地做这件事,甚至将医生的联系方式给我,让我去检查身体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件事竟然距离我这么近。
我一向觉得自己很叛逆,总是很独特独立,但是当这件现在看起来惊世骇俗的事情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慌张,甚至有一点点恐惧。我确实喜欢孩子,喜欢家庭,但是我一直认为,我应当有一个固定的顺序,我要先成为配偶,先拥有新的家庭,然后才可以有一个孩子。我要先当新娘,当妻子,然后才可以成为母亲,但是现在这个环上缺失了一段,以一种人力胜天的方式直接赋予我母亲的身份,我要一下子变成妈妈了。
我焦虑地无法入睡,父母和我说的各种话都让我对进入新身份望而却步,我不知道这件事做的对不对——我掌控我自己的生活,我明白我的所需,但是我能保证即将到来的生命对这样的人生感到满意吗,我要用谎言欺骗他们多久呢,他们是否能接受自己生来残缺的家庭呢,如果因此让他们痛苦,我会不会后悔呢。这些都令我感到莫大的责任,都让我觉得难以接受。
我偷偷哭了好几天,但父母却非常有行动力,他们甚至已经安排好了各种细节,包括去哪里生孩子,养在哪里,去哪里上幼儿园,我要怎么请假,仿佛这些他们早已考虑了很久很久了,现在终于可以着手施行了,对于即将要到来的孩子他们比我更加兴奋。
或许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去做比去想更为重要,或许他们经历的太多,知道许多事总有解决的办法,发生了,去解决就行,但首先得发生,或许他们对于未来比我更加乐观,或许是我和弟弟让他们对我们的孩子充满了信心,觉得一定不会有问题,一定是很好很好的未来。
许多年前,父母逼迫我相亲结婚的时候,弟弟只是说,人都有自己的缘分,她现在不想,或许就是月老的缘分不到,不用太着急,再说,就是有些人一辈子没有缘分又如何呢——到了现在,尽管我们没有正面谈论过这件事,但是父母也都和他说过了,他也支持——谁愿意自己的姐姐无依无靠呢,就像我也希望他拥有幸福的生活,幸福的方式很多样,但只要幸福就好了。
四月的时候,爷爷奶奶请人来做棺材,这是我们那里的风俗,人活着的时候盖好自己未来的房子就不怕死后无居所了,也是一种冲喜的方式。我和父母都参加了仪式。那天夜里,爷爷奶奶让我在新做好的棺材里躺了一会,说是一种风俗,珍贵的孩子在新棺材里躺一躺就能增寿添福,而我八字硬,睡一睡,或许就能找到好的依靠了——我以为棺材都是很小很小的,但躺进去的时候,竟然比意料中宽敞一些,我躺在里面,没有害怕,因为当我仰面朝天的时候,看到的是父母和祖父母的脸——外公这样躺着的时候,冥冥中或许看到的就是他至亲之人的脸庞吧。这一方小小的天地,这至亲之人的脸庞,爷爷奶奶会看到,父亲母亲会看到,而我,也会再一次看到。
我并不害怕。
发布于 2023/06/06
归档于 劝进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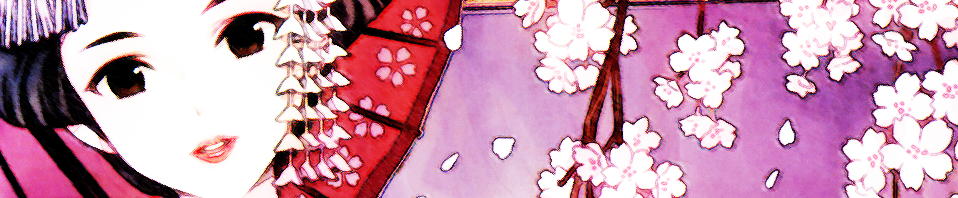













No Comment.